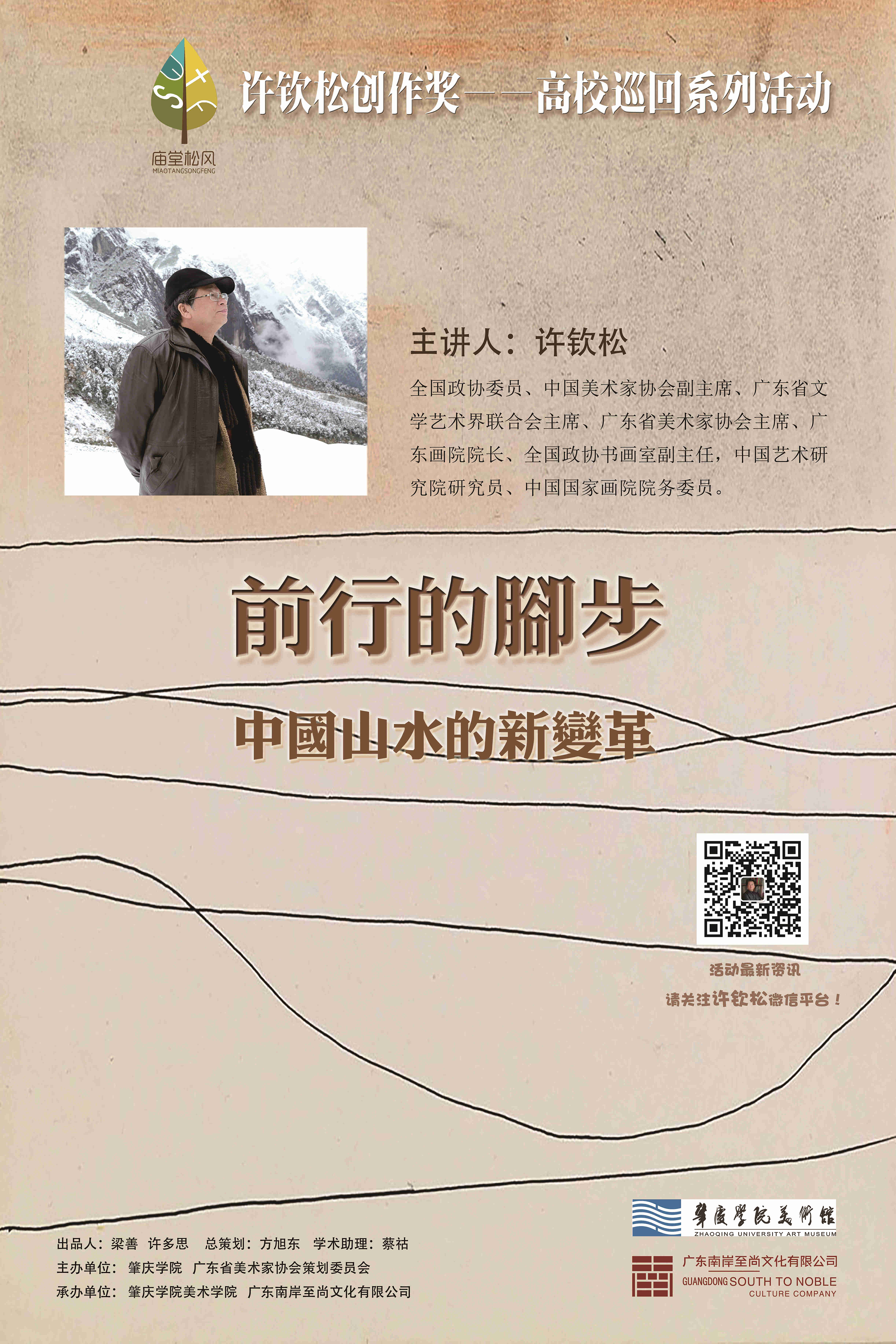
2014年10月13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广东画院院长许钦松先生应邀在肇庆学院图书馆学术报告厅为肇庆学院广大师生做了一场名为《前进的脚步:中国山水画新变革》的讲座。本次讲座是许钦松先生在广东省八大高校讲座的第一站,出席当天讲座的领导嘉宾有肇庆学院党委书记曾焕松、肇庆学院校长和飞、原肇庆市文联副主席邬邦生、肇庆市美协主席莫肇生、兄弟院校的同行以及社会各界的朋友。在主持人许多思简短的介绍后,许钦松先生在讲座中讲述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历史及艺术特征,其中包括山水画在魏晋的起源到隋唐的发展,再到两宋的崛起,元代的转折,明清的衰落直至近现代山水画的变革,肯定了岭南画派在中国近现代美术中的变革作用,同时分享了自己的山水画创作经验。
以下为许钦松先生的主要讲话内容:
许钦松:今天很荣幸与肇庆学院的师生们见面并进行这样的交流,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在一个亲近大自然的环境中长大,阳光、土地、雨水……大自然给了我很多创作源泉。我小时候开始接触美术,教我画画的是乡下里不是正规院校毕业能画几笔画的美术爱好者,到了小学、中学,有美术老师,后来到了县里的文化馆,我有机会接受正规的美术教育,再后来有机会考进广州美术学院,能够在大学里面接受教育。之后到了工作岗位,又有与很多大师接触并聆听他们教导的机会,比如李可染先生、吴冠中先生、关山月先生、黎雄才先生、赖少其先生、刘海粟先生等众多艺术大师都跟我有很深的交情,我在他们的教导下逐渐成长。我感觉自己是很幸运的,有这样的机会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坚持走到今天。在今天的讲座中,我主要想对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历史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并分析我山水画的艺术特点以及分享我自身的创作经验。
一、中国山水画历史
许钦松:中国山水画是由古代知识分子一手开创出来的,中国山水画最早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宗炳写了一篇山水画画论《画山水序》,这篇理论开始了对山水画的理论指引,这篇山水画论虽然只有两三百字,但很有见地,意义深远,它是中国山水画起步阶段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宗炳山水画论开篇指出“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像。至於山水,质有而趋灵”,可见中国山水画一开始就是形而上,这是非常了不起,就是这样一位大贤者,开启了中国山水画的历史进程。不仅如此,中国山水画还有一整套的绘画理论,包括为什么要画山水画、如何画山水画、如何去欣赏山水画等关键问题,名仕王维也曾论证过山水画的一些问题。西方人要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开始画风景画,可见中国人对山水风景的表现要比西方人早1000多年。
中国山水画是由知识分子从理论上提出来的,到了隋唐时期,当时的画家完成了山水画技法的积累与承变。从现存展子虔的《游春图》可以看到,虽然山水画受到士大夫的偏爱,但是唐代的山水画还是不能很好地解决山水画的绘画语言问题,此时的山水画绘画语言还是比较粗糙,并没有完善,整个唐代几乎都在解决如何表达山水的技法问题。唐代主要出现两种山水画风格,一是大小李将军父子,李思训和李昭道开创的青绿山水,二是王维开创的水墨山水。当然,说到开创也不完全是他们的功劳,而是当时画家的绘画相互影响而慢慢确立的某种风格,当时的吴道子、张璪也曾画过水墨山水。王维之后有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等绘画理论,这都是很有代表性的绘画理论。
中国山水画崛起的第一个高峰是在宋代,在整个山水画进入宋代崛起之前,我们有必要提及唐末五代。唐末五代大概只有短短的60年,时间虽短,但凸显了一大批有作为的山水画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山水画已经初步形成了南北派不同的风格,而且出现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山水画理论,就是荆浩的《笔法记》。《笔法记》里面提出了“六要”,即山水画的六大要素“气、韵、思、景、笔、墨”,对山水画的创作做出了理论的指导。“气”与“韵”是谢赫“六法”中的绘画总原则,“思”与“景”是山水画家思维与景物之间的关系,提出山水画家要度物象而取其真,“笔”与“墨”是更本质的概念,在以往的山水画论里,笔墨都是以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提出来,《笔法记》当中对笔墨问题做了非常详尽的探讨,并明确提出笔墨作为山水画的一个基本要素。五代画家荆浩与关仝的北派山水,荒凉干枯、气势雄伟,而董源与巨然的南派山水,把江南温润的气象、平静秀丽的景色很好地表达出来,南北画派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
到了两宋时期,中国山水画进入了最辉煌灿烂的王朝,不仅是山水,包括花鸟、人物绘画,都是全面兴起。宋代宫廷画院的体制,把一大批优秀艺术家调到宫廷里从事专业的创作,经过山水画家的不断推进,使得中国山水画在宋代达到很高的水平。宋代的画院制度在往后的朝代里一直都有延续,而且到了清王朝的时候,宫廷画家的行政级别很高,高的可以达到一品,宫廷画院给中国画发展带来体制上的保障,推动了艺术发展。北宋时期,有李成、范宽、郭熙等一批山水画大家,其中李成是一位标杆式人物,史料记载,当时很多画家向他学习,受其影响。北宋中期,郭熙的《林泉高致》提出了一些山水画创作的要求,将山水画的构图做了总结,提出“三远”的原则,即高远、深远、平远,提出了山水画的构图方法及欣赏视点的问题,并由这样一个构图方法来指引欣赏山水画的视点要求。北宋时期还有沈括的《梦溪笔谈》,里面有提及批评李成山水画的内容,但都不动摇北宋时期一大批山水画家在历史上的地位。到了南宋,马远、夏硅的院体山水画充满典雅的气象,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元代是中国山水画的高峰,元代山水画的风格与宋代大异其趣,主要原因在于文人画跃居为画坛主流,跃居为美术史主流。中国绘画建立在士大夫的审美基础之上,但是在元代之前的朝代并没有特别地强调,到了宋代后期,以苏东坡、米芾等为首的文人士大夫开始以宋代院体画为参照,提出新的文人画概念,文人画开始正式进入画史。如果说苏东坡标榜的文人画观念在宋代只是供士大夫偶尔为之,那么在异族统治的元代,文人画就是知识分子孑然不可侵犯的精神领地。因此,元代文人画更多地体现士大夫的道德精神,几乎占据了整个元代的山水画史,这种高尚的道德操守和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形成群体性的艺术实践,使得这个时候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画家。
明清时期是封建王朝进入没落的时期,绘画也体现大致的特点,一些山水画家跟宋元大家相比相差很大。明代山水画有董其昌、沈周这样的代表,董其昌的山水画成就极高,他也是一位书法家和艺术理论家,提出了“画分南北宗”的重要绘画理论,但即便如此,其绘画也无法超越前人的艺术成就。清代的山水画更是每况日下,董其昌的继任者,如以“四王”为代表的正统画派,虽然朝廷将其标榜为正统画派,但山水画已日渐走向衰落。
整个朝廷的文化气象跟民族、国家的气象是相通的,一个国家昌盛,其文化才能昌盛。到了清末,爆发了辛亥革命,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我不得不提岭南画派,清末民初,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岭南画派“两高一陈”在这样一场革命当中提出中国画的革新,如折中中西、融汇古今、关注现实、注重写生等一系列绘画理论,在清末中国画走向没落之时,为中国画走向现代找到了一个发展方向。历史上对岭南画派的评价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在清末传统文化走向没落之时,岭南画派刮起了这场革命,而且“二高一陈”都是国民党的元老,加上政治的力量,岭南画派影响了整个中国及海外。岭南画派的理论体系逐步为广大的美术界所接收,其绘画理论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理论是想通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岭南画派的绘画理论对主流美术带有理论指导意义,但发展到现在,在改革开放以后,岭南画派这么一个革新的理论、一个很独特的地方画派理论在被全国美术界所接受,由一个个性理论变为共性真理以后,岭南画派反而被淹没了。近十年来,我们重新高扬岭南画派革新的旗帜,重新出发,把我们岭南画派的艺术再度弘扬起来,并且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学术活动以及展览的开办,使岭南画派再度为全国所关注。
二、许钦松的山水画创作
许钦松: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曾临摹《芥子园画谱》,还装订成册,这是我小时候正式学习中国画的开端。后来,我有幸到了澄海市文化馆学习木刻,考进广州美术学院的时候被分配到版画室。我是1972年进入广州美术学院,当时我们的专业设置是一专多能,除了版画老师给我们上课以外,还有王肇民先生教我们水彩,黎雄才先生教我们国画山水,杨之光先生教国画人物。当时我在大学里面主要学习版画,但对国画的学习一刻都没有放松,对国画保持了一个长期学习的过程。我的版画作品在一个时期密集地大量发表并且大量获奖,因此大家知道我是一个版画家。而作为一个国画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我的第一个个展不是版画展,而是在香港举办的一个山水画展,后来我的山水画展先后多次在港澳台及海外展览。在内地,大家更多地知道我是一个版画家,而很少知道我在海外广泛传播我的山水画。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被选为广东省“跨世纪之星”,成为省里宣传文化思想战线的接班人。这次评选作为省委宣传部的重头戏,在广东美术馆给我举办了一个版画展,也出版了一本画集,从那一年开始,我就基本结束了我的版画创作,全面进入了山水画创作当中,一路走到今天。
我创作的山水画特点很明显,个性非常独特,很多人远看就能认出我的作品。我的山水画既有传统的一面,也有革新的一面。在古代,山水画曾经安置了古人的灵魂,让文人墨客在其中找到精神归宿,他们的神思可以遨游于山水丛林之间,山水画成为精神的家园。我山水画的精神追求与前人有很大不同,我的山水画没有出现人,人迹稀有,甚至连房子也没有,一片荒芜,反映了大自然最原始的状态,表现的是人类没有到达的地方,这样的山水画是圣神的,可望不可即。因而我有一本名为《此岸彼岸》的书,我们是站在原地遥望自然,把自然推举到一个高度,一个推崇膜拜的对象,而不能去惊扰它,这是我山水画思想独特的地方。古人的山水是可望、可即、可游,是享用大自然,我所不同的是排斥人类对大自然的干扰,让自然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带有一种宗教情怀,一种膜拜的心情去面对自然,这是对当代山水画的新思考,这种思想贯穿在我整个艺术创作里。这种思想在以往的山水画创作中是不存在的,从我的山水画创作开始出现对新时期山水画思想的一种思考。美术理论家薛永年先生曾评价我的画为“广远”,这是与古代山水画的构图、视觉做对比得出的结论,宋代画家郭熙曾提出“三远法”,高远、深远、平远,“广远”是指视觉得到极大提升,仿佛作者和观者凌空穿行其中,在广袤的视野当中环视大自然。因此,我的绘画既不是传统绘画的散点透视,也不是西洋绘画的焦点透视,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环视透视法”,我不是从固定一个点看山,而是可以从各个方向看,环视大自然。这样一种奇特的感受来自我上世纪90年代到尼泊尔的一次访问,当时坐着小型直升机在高空俯瞰尼泊尔皑皑雪山,感到非常震撼,山峰纵横千里,这种深远的感觉是古人山水画里从没表现过的,我顿时豁然开朗,后来经过无数次锤炼、实践,形成了我现在的“环视透视法”,用一个很宽广的视野回望山川。看待人与自热的关系,应该要超越人类本身,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人与自热,强调自然是可望不可即,不可以去干扰破坏自然,甚至去污染她。这样的思想角度恰恰暗合了人类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就是我们的地球未来会怎样,我们的身存环境以后会怎样。正因为我的山水画恰好跟这个时代主题相吻合,使得我的山水画引发很多人的关注,包括部分思想界的人。
我的绘画里吸收了很多西方绘画的创作元素,也吸收了版画的创作经验,我一开始做中国画研究,在探索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人说我画得像版画,而不是中国画。在创作中国画的探索过程中,版画的创作经验既是我的优势,也是我的劣势。这是两个画种,但在语言方面又有可融合的地方,版画和国画在印刷术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双胞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如佛经的插图,也是先用线描绘制出来,再刻到木板上去印刷。学习书法的人为什么要临碑帖,这些刻在石头上的书法原本就写在纸上,但拓成帖后与书写在纸上的书法又不一样,因为通过二度创造,让书法带有金石味,而金石味在国画里是一个很高层次的东西,它与刻字有关,跟木头、石头有关。这恰恰被我找到版画进入国画最优势的地方,就是把版画里强有力的金石味引入我的国画技法中,正是这样的引入使得我的中国画具有一种雄壮的力量,就像刀刻出来、斧头劈出来一样,具有一种力量感,符合了中国画最高的一个审美标准。版画的创作经历让我找到了进入国画创作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结合点,对于西方绘画的光色变化,由于我曾学过油画、水彩、水粉,有良好的色彩训练基础,中国绘画的色彩关系长期以来被固化为一种模式,因而我把西画里微妙的光色变化引入到中国山水画,这是我吸收西洋绘画元素有所创新的地方。
水墨在中国画里早已被人作为研究的对象,很多美术理论家都在研究中国画的笔墨问题,但我发现墨色的变化永远无法达到我们想象的丰富。我们很多国画家在创作时并没有把墨色发挥到极致,就像钢琴的最高音和最低音,我们的画家在创作时只用到了其中一部分,还有相当多的层次没有表现出来。我用了十几年的功夫,为表现墨色的高度丰富做了大量实践,水墨的厚重与灵动是一对天生的敌人,很多时候画面厚重了就无法灵动,灵动了又无法厚重,过于厚重会死板,过于灵动就会显得轻飘。如何把厚重和灵动统一起来是我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学术点,如果我突破了,我的艺术创作就能向前迈出一大步。在国画创作中,黑色不等于厚重,就如一块木炭,看上去很黑,但拿到手里一点都不厚重,但一块黑色的玉石,色泽也很黑,放在手里很厚重,但这沉甸甸的石头用光一打,却是灵动的,能看到光在闪烁以及纹理的变化。让画面既厚重又灵动是我目前水墨画的主攻方向,为此我做出了很大努力,并且创作出一批大家认同的作品。
许钦松先生讲述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脉络,并分享了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创作经历与体验。在讲座过程中许钦松先生还与同学们积极进行互动交流,耐心解答同学们提出的关于艺术创作的问题。许钦松先生的讲座为肇庆学院师生带来中国山水画当下最新的发展状况,对于肇庆学院师生增进对中国美术史的了解、拓宽艺术眼界、提高审美趣味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